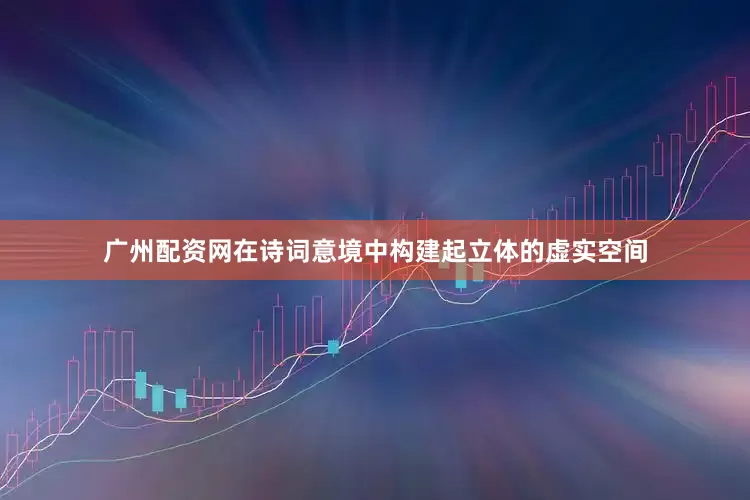
格律诗词创作的意象美学
作者:王湛梅
格律诗自盛唐气象中淬炼成型,以精妙的声律图谱重塑汉语诗歌基因。平仄、押韵、对仗作为格律诗词的三个基本要素,为其奠定了严谨的形式基础。至宋朝时,词迎来空前繁荣,与格律诗共同构筑起古典诗词的璀璨星河。然而,意境才是穿透这些形式美学的核心密码。在千年文脉的滋养下,格律诗词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意象经营法则,通过虚实相映、动静相宜、情景相融、正侧相谐四大法门,构建起中国传统诗词美学的艺术空间。
一、虚实相生:笔墨之外的留白艺术
古典诗词的虚实之妙,在于“无画处皆成妙境”。李太白笔下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,将一叶扁舟的实体意象融入天际的虚空,在虚实相生间勾勒出无尽的离愁别绪。李商隐《无题》中“蜡炬成灰泪始干”,把实体的蜡烛虚化为泪水的意象,在虚实转换间编织出迷离而深邃的意境。这种艺术手法恰似水墨画的留白,于具象与抽象的交界处开辟广阔的想象空间,使有限的文字承载无限的意蕴。
笔者的《青玉案·两地情》:“数年枕上边关处,沐霜雪、山间树。风去风来沙影暮,寒凝戈壁,烟迷尘路,惟愿长城固。 冰轮携梦家园去,杨柳依依岁华误。试问妻儿何与度?千般琐事,几番停伫,堂燕声如诉。”上阕以“霜雪”“戈壁”等实景描绘边塞风物,下阕借“冰轮携梦”虚化相思之情,更以’堂燕声如诉’作为虚实转换的枢纽——燕鸣既是对梦中实景的描摹,又是对离别情思的虚写。此处虚实嬗变,暗合《园冶·兴造论》中“虚中有实,实中有虚”之妙。通过“烟迷尘路”与“岁华误”形成时空交替,既给予读者强烈的视觉冲击,又触动其情感共鸣,在诗词意境中构建起立体的虚实空间。
再如拙诗《观照》:“屏前旧照翻,寸寸光阴辙。轻拭那人颜,心弦成纸屑。”“旧照翻”与“轻拭”为动作写实,而“寸寸光阴辙”“心弦成纸屑”则是虚写。通过虚实交替,巧妙唤醒读者的共情体验。诗词与书法在艺术规律上相通,用笔过虚易流于浮滑,过实则显凝滞呆板,唯有虚实结合,方能使作品兼具稳重与灵动之美。
二、动静相宜:时空流转的诗意捕捉
在诗词美学的体系中,动与静犹如太极的阴阳两极,相互激荡,在平衡中产生独特的韵律之美。杜甫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”两句,以垂天之星辰的恒久静谧,与奔涌江月的动态流转相映成趣,在动静对比中展现出天地的浩渺苍茫。
这种动静相生的艺术哲思,在王维的诗作中达到极致。“明月松间照”勾勒出静谧的画面,随即以“清泉石上流”注入灵动之感;“竹喧归浣女,莲动下渔舟”的声音与动态描写,更添生活气息。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”则以动态的“落”字反衬春山的幽静,“惊”“时鸣”等动态描写同样精妙。这般笔法如同水墨画中的枯湿浓淡,在动静的平衡中踏出诗意的韵律。
回顾自己的学诗历程,初学时因不擅运用动词、描写动态景物,作品常显呆板。后逐渐领悟,唯有动静结合,方能赋予诗歌鲜活的生命力。如拙作《五月》:“夏声莺自传,枝上绿浓抹。风过一痕轻,春绯谁扫脱。”通过莺声、“抹”“风过”“扫脱”等动态描写,打破写景的静止感。再如《风入松·初秋荷塘》:“水轩烟雨似生凉,依旧荷香。纵然减却红颜色,参差处、绿盖煌煌。娇态倚风曲港,多情照影秋光。 笑看纤手弄沧浪,最是繁忙。珍珠拨断还重聚,探身去、欲摘莲房。折下团团玉叶,裁成袅袅霓裳。”上片描绘静景,下片刻画观荷人的动作,即便在上片静景中,也以“减却”“倚”“照影”等词增添动态,使作品在静谧中蕴含生机,在动态中保持诗意平衡。
图片
三、情景相融: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
宋人范晞文在《对床夜语》中提出“景无情不发,情无景不生”,并以杜甫的诗为例进行分析:“天高云去尽,江迥月来迟。衰谢多扶病,招邀屡有期。”上联写景,下联抒情;“身无却少壮,迹有但羁栖。江水流城郭,春风入鼓鼙。”上联抒情,下联写景;“水流心不竞,云在意俱迟。”是景中含情;“卷帘唯白水,隐几亦青山。”为情中见景;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。”情景交融,难以分辨;“白首多年疾,秋天昨夜凉。”“高风下木叶,永夜揽貂裘。”则是一句情一句景。可见,情与景并非简单相加,而是如同氢氧结合为水,浑然一体。我们写景时,自然融入喜、怒、哀、乐等情感,以及对景物的褒贬态度,正如王国维所言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;我们在抒情时,又常寄情于物、借物传情,因而“一切情语皆景语”。
苏轼《水调歌头》中“转朱阁,低绮户,照无眠”,将月光流转的景象与词人辗转难眠的情思完美融合;李清照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、点点滴滴”,把萧瑟秋雨与寂寥心境交织成细密的愁网。拙作《清明》:“年年最怕近清明,陌上残花伴墓茔。唤起心间那丝痛,空叹春色太无情。”以“残花”“墓茔”渲染清明的伤感氛围,借春色“无情”抒发内心痛苦。《南乡子·侍母游陶瓷水镇》:“窑釉流霞彩,笼盔刻岁斑。晴澜淬碧载天然。手挽萱堂徐步、绽欢颜。 轮仄台阶陡,身倾耄耋蜷。刹那风滞魄如寒。细拂襟尘重倚、暮云边。”上片写景烘托母亲的愉悦心情,下片“暮云边”既暗示母亲年事已高,也传递出母子相依相伴的深情。这种移情入景的手法,让自然物象成为情感的载体,在情景交融中构建起深邃的抒情空间,赋予抽象情感鲜活的生命力。
四、正侧相谐:多维视角的诗意构建
柳宗元《江雪》全篇描绘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的雪景,却在结尾以“孤舟蓑笠翁”收束,通过环境的侧面烘托,突显人物的孤高形象。这种侧面描写的手法,恰似中国园林的框景艺术,以迂回的方式增强表达效果。
李白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,朝如青丝暮成雪”,以夸张的侧面描写展现时光流逝的迅疾;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“五陵年少争缠头,一曲红绡不知数。钿头银篦击节碎,血色罗裙翻酒污”,通过他人的追捧衬托琵琶女的美貌与才情。拙诗《贺九华诗社一周年》:“九华灵峻上高峰,相约白云诗味浓。春去春来花更好,含英采玉自从容。”借九华山的高峻凸显诗社的格调,以“白云”象征诗社的纯净,用“花更好”展望诗社的美好未来。以侧映正、以虚写实的手法,使诗词在创作中形成多声部的共鸣,极大拓展了艺术表现的维度。
在虚实相生、动静相宜、情景相融、正侧相谐这四大艺术法则的交织下,中国古典诗词构建起独特的意象美学体系。历代诗人在虚实的变幻中挥毫泼墨,于动静的交替间勾勒意境,将情景交融的韵味与正侧相谐的视角熔铸为永恒的诗意。作为学诗者,深入领悟并灵活运用这些法则,方能叩开古典诗词艺术殿堂的大门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唐山股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